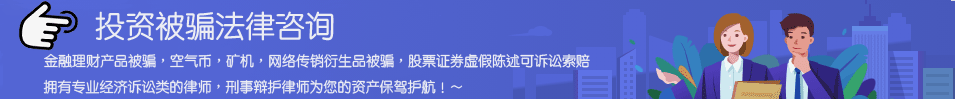1980年12月1日,成都市公安局接到某军工厂保卫科报案:本厂实验车间的一个价值43000多元的实验用铂金坩埚在11月30日发现被盗,全厂动员寻找一天一夜未果,只好报案。
成都市公安局三处接报后迅速派遣侦技人员赶到某军工厂勘查现场,最后一个接触被盗坩埚的是一位女助理工程师,她说:11月15日她做完实验后,将坩埚和搅拌器放入砌在地面上的一个方箱状的陶瓷酸洗池浸泡,但是11月20日她再去取用时,发现池子里已经空无一物,当时她以为是被其他人拿去用了,并未在意,反正实验也不是很着急,等等就等等。但是她一连等了十天都没见过这只坩埚,这才起了疑心,并向厂保卫科报告。保卫科查了一天,确定铂金坩埚被盗。

使用中的铂金坩埚

铂金坩埚
这只铂金坩埚只有一只茶盅的大小,且因为经过反复试验,表面已经附着了陈旧的实验遗留物,外表凹凸不平且浑身呈铁褐色,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铁罐罢了,外人根本不清楚这只坩埚的价值。但这只坩埚是整个实验车间公认的“金娃娃”,所以当得知“金娃娃”被盗后,全厂震动。
由于发现坩埚不见的时间是11月20日,报告保卫科的时间是11月30日,中间相隔了10天时间,在这十天里,现场人进人出,已经完全被破坏,使得现场勘查一无所获,群众走访一圈下来众人也表示隔了十天了,就算有人进过实验车间把坩埚拿走,那也是记不起来了。因此,虽然警方认定这肯定是一起内部人员作案或者内外勾结作案,但却大有无从下手的无力感。
由于铂金在国内当时并不能买卖变现,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卖到国外去才能变现,最可能是就是先运到沿海或者沿边省份后偷运出境。这种排查工作量大不说,以当时的条件下效率却十分低下,只能结硬寨、打呆仗,一条一条的渠道和线索逐条排查,这一查就查了一年。
……
通过一年的排查,“金娃娃”案破案小组通过艰难地排查,终于将侦查目标圈定在几个往返于成都和广州之间的“阔仔”上,在对他们上了侦查技术手段后,监听到了如下讯息:
“白花蛇已遇良机,尽快送来。”
“我将出去一趟,请回东家。”
“白豆鉴定无误,人货一到即付款。”
围绕着这些讯息背后露出来的线索,侦查员们辗转于广州和成都两地,对这伙“阔仔”实施严密追踪。
……
1981年11月16日,广州珠江边长堤大道上,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行迹鬼祟。胖子西装革履,是澳门一家商号的经理,瘦子绰号“海仔”,是香港澳门和内地走私渠道的“中间人”,经长时间跟踪确认,这两个人应该就是“下家”和“中人”。而“海仔”在成都有一个绰号“虎头”的“牵线”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青年,根据对通话的监听,这三个人将在11月19日在广州见面,为的就是“白花蛇”。这个“白花蛇”是他们谈论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应该指代的是他们要交易的物品,但到底是不是被盗一年的“金娃娃”铂金坩埚还需要核实。
11月19日,胖经理、“海仔”和“虎头”在广州郊外的一家西餐厅里会面,胖经理带来了一只胀鼓鼓的提包,将提包放在餐桌上拍了拍,向“虎头”比划出了四根手指头,“虎头”顿时兴奋地手舞足蹈,甚至碰倒了面前的酒杯,红酒洒了一桌子。但是当胖经理向“虎头”索要“白花蛇”时,“虎头”却长叹一声,颓然靠在椅背上,显然“白花蛇”不在“虎头”身上。接着,三个人撇下了满桌子没动几筷子的珍馐美味出了餐厅,在一个僻静处头顶头地耳语了一番后各自散去。
当晚,“虎头”从广州白云机场登上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离开广州——

老照片:广州老白云机场航站楼
……
11月22日16时30分,一架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三叉戟”客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一名身材魁梧的男青年最后一个走出机舱,他站在舷梯口向四周探望了一阵后才故作镇静地下到停机坪,他正是“虎头”。

老照片:80年代的成都双流机场

中国民航的“三叉戟”客机
但是,当他还没走进航站楼,就被两个民警拦住去路:“同志,你乘错飞机了吧?”
“虎头”愣了老半天,回过神来后掏出了首都机场的102号登机证,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是去北京探亲回来……没有到过其它地方。”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前几天不是还在广州和人聚餐吗?”
“虎头”如遭雷击,整个人都蔫了,只好乖乖跟着民警上了一辆吉普车——
11月24日,“海仔”在广州火车站被广州市公安局的侦查员“请”回局里,然后被押上一架“三叉戟”送回了成都。
“虎头”是当时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某大厂当技术员,是厂里公认的业务尖子,但其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想要去美国定居,为了筹措出洋经费,不惜违法多次进行走私活动,几次下来已经成了一个颇为“上道”的“掮客”。
“海仔”是广州人,原本是个医生。但羡慕于“有海外关系”的同事成为单位里统战部门的“红人”,自己也想“攀结海外关系”,结果阴差阳错地成了走私“掮客”。
“虎头”和“海仔”交待说:半年前,一个绰号“小猴”的人找到“虎头”,央求他帮忙寻找门路转卖一个两斤半重的铂金坩埚,为了确定质地,“小猴”在两个月后交出了一颗黄豆大小的样品给“虎头”,并再三叮咛:“听说别人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搞到手的,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真正的货主是谁,我也不敢去打听。”
“虎头”将这块样品交给了“海仔”,由“海仔”将其带到澳门,经鉴定系高纯度的铂金,于是胖经理心动了,专程来到广州招“虎头”见面,出价40000元希望收这个铂金坩埚,为掩人耳目,他们将这个铂金坩埚称为“白花蛇”。
警方判断,“白花蛇”应该就是成都被盗的铂金坩埚。鉴于狡猾的“货主”还没露头,警方决定采取分化利用、深入其内的策略,诱使“货主”露头。
……
1981年2月17日17时,成都的人民南路广场,一个身穿军用棉大衣的男青年左顾右盼地走到毛主席像前,与一个早已等候在此的高个子耳语几句后两人就分手转向,分别沿着毛主席塑像基座两侧进入展览馆,先后闪进了一间厕所……

成都的人民南路广场
18时05分,两人又结伴来到成都饭店二楼的餐厅,就坐几分钟后,那个穿军用棉大衣的男青年将棉大衣脱下占据了座位,然后匆匆下楼离开……

成都饭店
18时20分,这个人来到东御街的市内火车票售票处门前和一个神情紧张的大胡子会面,从他手中接过一个沉甸甸的黄色挂包后两人就分开了,全程没讲一句话。
18时30分,该男青年带着黄挂包回到成都饭店二楼餐厅,向那个高个子男青年点了点头,然后将黄色挂包往餐桌上一放,露出了一截银白色的金属管,高个子看了一眼就极度紧张地抓起椅背上的棉军大衣将其盖住。
……
两人吃完饭后,穿棉军大衣的男青年先行离开,而高个子看着他下楼后才背起黄色挂包离开,但当他刚出街口时,就被三名便衣侦查员截住,“咔嚓”一声戴上手铐。从他背上的黄色挂包内缴获了铂金坩埚一只和同样铂金质地的搅拌器,根据高个子的交代,那个穿棉军大衣的男青年就是“小猴”——成都某大学在校学生,还是学校的共青团干部和共产党员——
当天深夜,侦查员冲进了“小猴”的家里,将“小猴”堵在床上,并根据“小猴”的交代在2月18日凌晨抓到了向“小猴”递送黄色挂包的“大胡子”男子。“大胡子”一开始装傻,但“大记忆恢复术”之下很快供出了他的上线……
在一连转了五个“上线”后(全部是成都的国营企业职工,“下水”的原因都是为了结婚、女方的要求高而要筹措高额的彩礼),终于查到了这条线的尽头——案发单位实验车间熔炼工曾焕文,这名隐藏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窃贼终于落网。
曾焕文被捕后很配合,其供词如下:“我们车间大家都知道铂金坩埚值几万元,但上上下下又有人认为这样贵重的东西没有哪个敢偷的,偷了也卖不掉。因此取用、保管都很随便,有段时间还丢在车间外的空地里,甚至还有人将这东西抛来抛去开玩笑说:这个金娃娃拿去发财噻!”
“1980年以前,我从来没想过偷这个东西,后来听说社会上搞金银走私很来钱,就动了心,而且我正和我对象准备结婚,我打算给她个高标准的婚礼,手中缺钱。但是我试过几次都不敢下手,又转念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麻痹,我真的偷了也不会有人想到被偷了,反正公家的东西没人心痛,说不定追查一阵后就不了了之了。”
“1980年11月18日上夜班,我从酸洗池前经过,看见四下里没有别人,就讲铂金坩埚和搅拌器从酸洗池里捞了起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挂包,下班时挟在腋下混出厂藏在家中。”
“作案后我心情很紧张,但注意观察了十天,车间里都没什么动静就放心了,后来看到保卫干部和公安在车间里进进出出,因为害怕暴露不敢销赃。半年后,我想搞一万元跟我对象办个高标准的婚礼,才不顾一切,转了几道手托人将坩埚变卖,唉——没想到啊,这就被你们抓到了。”
最终,曾焕文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老虎”和“海仔”因走私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二十年;“小猴”和另外五个“中间人”因销赃罪被判处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